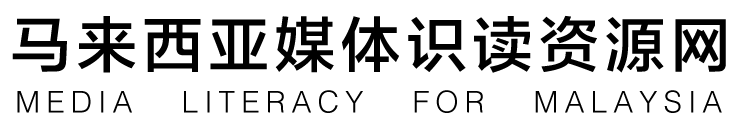作者:邓晓璇,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中国) ‖ 下载PDF档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诽谤法令在马来西亚传播实践中的现状,并分析诽谤案例中高额索赔对传播的负面影响。
诽谤与传媒的关系,就好像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孙悟空与其头上的紧箍圈那样,比之更甚的是,这个紧箍圈就像是媒体身上自然生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国的情况皆大同小异,没有“松箍咒”可把它解除。各国法官在诽谤官司中,对维护个人声誉或是维护新闻自由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诽谤法令的作用是保护个人声誉免受不真实的言论侵害,但近年来,困扰着马来西亚司法界及传媒的问题是,诽谤诉讼中起诉人的索偿额日益升高,于是又引起诽谤威胁了新闻自由的争议。在尊重人身自由与维护言论自由之间,传媒是否能找到平衡点?
一、马来西亚的诽谤法令
根据诽谤者的表现形态及不同的手法,马亚西亚的法律和英国一样,把诽谤分为文字诽谤(Libel)与口头诽谤(Slander)。
口头诽谤是指非永恒性及非固定性诽谤,比如话语、手势、聋哑人的手语等。发表物的存在形式是临时的、暂时性的。[1]马来西亚诽谤法令就规定口头诽谤在一般情况下必须证明起诉人所蒙受的特别损失(SPECIALDAMAGES),才能构成起诉行动,而其无需证明特别损失便可采取诉讼的四种情况则在此略之。
如果翻开各国的诽谤案例,口头诽谤的案件并不常见。由于人们都习惯把注意力投射在知名人物的身上,于是知名人士对自身声誉也最敏感,他们最容易证明自己在口头诽谤中蒙受的损失。
文字诽谤是指具诽谤性的话语或文字是存在于永久性或固定性的形态,因此也被称为永久性诽谤。它主要指一些永久性存在的发表物包括印刷物、相片、绘画、雕像、肖像、蜡像、墙上的粉笔字迹等具永恒性质的诽谤性意思。
电影集视觉及听觉信息于一身,其在电影荧光屏上所出现的画面却是短暂的、一瞬间便掠过的,然而电影胶片是永存性物质,于是被列为文字诽谤。同样地,对收音机及电视台的广播而言,由于现场直播节目可以把讯息传达给予更多的听众或观众,其造成的伤害可以和文字诽谤成正比。其传达的结果和文字一样,可以分布给一定人数,所以为文字诽谤。
马来西亚1957年诽谤法令第3条就规定:通过电波广播的话语必须视为永久性诽谤。文字诽谤无需证明起诉人的特别损失就能构成起诉行动。由于文字诽谤的表现形态较为宽广,各国的诽谤案件中,文字诽谤的案例也多得不胜枚举,而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媒体就是通过印刷品、漫画、电台广播、电视台、电影等来传播讯息的,因而文字诽谤对媒体的威胁及影响是最直接的。
笔者认为,电影及漫画都是现实的再加工、再创造,它们与新闻、评论不一样,一般受众在接受当中的讯息时都会有“作品含不真实、夸大成份”的心理准备,而不同受众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解读,每个人都应该包容艺术创造,动辄起诉漫画作者、电影工作者诽谤,只会扼杀了艺术的创作空间。
无论是文字诽谤与口头诽谤,其构成要件是(一)所公布的话语或文字必须是对个人或法人具诽谤性,答辩人有无意图并不重要,起诉人也无需证明他是否有此意图。如果是话语或文字的表面自然意义是含蓄的,这种影射(INNUENDO)也可构成诽谤,如果你说:“那几个兄弟姐妹不是一个爸爸生的”,可说是影射那些孩子的母亲不守妇道;(二)诽谤性内容的被诽谤对象必须指向起诉人;(三)话语或文字必须是在恶意的情况下发表的。针对这一点,一段诽谤性内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也常常令媒体百口难辩。
二、马来西亚的诽谤法令在国内媒体中的现状
诽谤法令就是旨在为个人的无形资产——声誉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当代英、美国家对诽谤罪的规定大都以“普通法”(Common Law)为依据,再由法官和学者来下定义,因此现在的诽谤官司几乎都是民事诉讼,要求金钱赔偿为主。
马来西亚曾是英国殖民地,诽谤法基本上是以英国法律为依据。目前沿用的是在1957年修正并通过的诽谤法令(称1957年诽谤法令),该法令和英国的1952年诽谤法令雷同。英国的法律是不成文的,也就是说,它是无数判例所形成的法律。
高额索赔蔚然成风
1994年10月22日,高庭判决自由撰稿人比莱、《马来西亚工业杂志》总编辑哈山及其出版及印刷商诽谤成功集团执行董事陈志远罪名成立,共赔偿1千万零吉(约人民币2千万元)。 2]这宗诽谤诉讼的起因是该杂志刊登了由比莱写作的诽谤性文章,该文章指陈志远通过裙带关系、官商勾结取得数项政府工程的合同。法官拿督莫达西汀在下判时说:“在研究了此案后,我发觉答辩人是串谋诽谤陈志远,因此诽谤罪名成立。”他在考虑诉方的崇高地位,此案的严重性,诽谤性文章的一系列报道方式,杂志的发行量,作者无法证实其言论,缺庭,拒绝改正,拒绝收回该文章,拒绝道歉等因素,做出上述判决。
“陈志远案”的1千万赔偿可说是开了高额诽谤索赔的先例。马来西亚的诽谤法令尚未定下最高赔偿额。上诉庭曾裁决起诉人可以列明所要求赔偿额。最后的判决是由法官一个人独自决定的,他可以考虑以本国其他的诽谤案判决为案例。陈志远案之后,入禀起诉媒体的案件不但明显地增加,索赔额更是漫天开价,令媒体穷于应付!1999年,陈志远再次入禀高庭诽谤民事诉讼,起诉道琼斯出版社等5方,索赔额总数达12亿5千万零吉(约人民币25亿元)。2000年,工程部长拿督斯里(注:“DATUKSRI”为一种荣誉封衔,由大马统治者颁予)三美维鲁起诉友谊印务公司和其他媒体,索赔1亿零吉(约人民币2亿元)。今年2月23日,一名外劳代理公司的董事起诉第三电视、马来西亚多家中英巫文报章,总共要求13亿零吉(约人民币26亿元)的赔偿。马来西亚诽谤案的前例中,还未超过20万零吉的赔偿。
显然地,陈志远案中传媒是最大的输家。1千万的赔偿当中,自由撰稿人比莱及总编哈山分别需赔偿200万及300万。自古“文人皆穷人”,在重商轻文的发展中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自由撰稿人赖以谋生的收入就是各报刊的稿费。以华文报的稿酬为例,一篇时评的稿酬约40零吉(约人民币80元),200万,可能是一名作家一辈子也无法拥有的积蓄。但对一名如陈志远的成功商人而言,他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赚回200万。那么以如此高额的赔款作为对传媒工作者诽谤的惩罚,笔者认为已经阻吓了传媒工作者的写作多于保障个人的声誉,如此高额的诽谤索赔对传媒工作者而言只不过是光明正大的“勒索”与威胁。
法庭是以补偿作为判决赔偿额的考量。当中的因素包括实际金钱损失、预计的金钱损失、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和对起诉人造成的痛苦和苦恼。马来西亚前联邦法院首席法官敦尤索亚曾提出:诽谤的天文数字赔偿不可与交通意外对人体造成的相对性低微赔偿相提并论,诽谤对人格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比的巨大。笔者觉得有关赔偿对于伤残者是非常不公平的。在1986年的一宗工业意外中,造成一人四肢瘫痪,赔偿18万零吉(约人民币36万元)。[3]如果说名誉损失对人格所造成的伤害会给被诽谤者带来无可弥补的精神损失,那上述瘫痪者一辈子不能工作,他所背负的精神损失与名誉受损的人相比,对一个正常人而言,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么18万和1千万就是肢体受损及名誉受损的差价,这个差价真的是太大了。再说,名誉受诽谤所带来的精神损失应该怎么去衡量?前任法官丹斯里哈仑哈欣曾指出,对诽谤诉方来说,在诉讼中胜诉已是一项很大的胜利,当事人也因此而挽回名誉,所赔偿数额不应过高。[4]笔者绝对赞成他的说法,法官的一句“你有罪”对一名誉受损的人而言应该是很神圣的,如果还要坚持用金钱的多少来表达“你的罪有多深!”只能表示诉方对司法失去信心,是严重的司法危机。
大马诽谤法令的不足之处
今年,从首相署部长莱士雅盯新任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丹斯里莫哈末赛汀阿都拉到大马律师公会新会长马永贵,无不把检讨高额索偿的诽谤案列为关注的重点,虽然各方舆论对是否应该进行司法改革或立法改革不尽相同,但各方立场的共同点,就是即刻修改已经被司法和法律界认为是过时的“1957年诽谤法令”,制定出一套符合当下环境的赔偿标准。
上述巨额索赔的案例显然的也是在过时的诽谤法令中产生的。很讽刺的是,马来西亚的诽谤赔偿不仅是共和联邦中最高的,也可能是全球最高的。[5]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修改法令、限制诽谤赔偿额应该是刻不容缓,以便给大马传媒一贴定心剂,不必每天在巨额赔偿的法律边缘提心吊胆,也可以防止被诽谤者食髓知味,企图从诽谤官司中得益。但是,由于已经有了案例,既使要限定数额,也似乎对传媒不利。法官不应允许起诉人列明索偿额,法庭更应该重视以起诉人的实际损失为衡量标准,在制定赔偿额时,更应该考虑大马传媒工作者的收入状况,在惩罚他们之余,不应把他们逼入死胡同。
马亚西亚的诽谤可构成刑事罪或民事罪。在民事法中,可以提出诽谤诉讼的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以及根据法律成立的机构或公司(法人)。2000年10月,首相向传媒发表“华文教育运动者是共产党”的指责,由于马来亚共产党在历史上被列为反动分子,所以,把人指为共产党是一种诽谤的言语,首相一席话引起华社喧哗,不过却不能告他诽谤,因为他并没有指向特定人士。构成刑事罪的因素为: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将发生伤害的情况下,仍有意地用言语通过口头或显而易见的话语、文字、信号,发表或印刷对某人的诋毁,破坏他的声誉。被告将由警方控上法庭,最高刑罚为坐监两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如果对一名死者的诽谤,将对假设还活着的“他”造成诋毁,或者有关言论是有意伤害其在世家属或亲人的感情,这将构成刑事罪[6]。刑事诽谤案在马来西亚的法庭极少见,对媒体的诉讼一般以民事法处理。
对法律而言,刑事处分固然是为了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对传媒工作者而言,刑事处分显然是太严重了!虽然马来西亚目前尚没有记者入狱的案例,但只要法律一日未划定界限,无论是对记者、编辑、出版商、印刷商,都有可能面对坐监至多两年的刑事处分,对任何一名传媒工作者而言,都似一颗计时炸弹。
现有的诽谤法令不仅对诽谤的定义及辩护理由都存在不足之处,对衡量名誉损失、人格尊严受侵所应得的赔偿概念也是模糊难理清的。律师公会在今年提呈的《诽谤案的言论自由影响报告书》中提到,在电子通讯时代,有权势者应对某些人指责的事物加以交待,同时他们应可以受到合理批评。[7]
在网络媒体发展迅速的今天,本来能与政府的新闻管制相抗衡,却出现网上讯息真伪难辨、难控制的问题。大马1957年诽谤法令制定时,根本无法预知今天的电子时代,然而我们看到互联网对传统言论自由的规范的冲击,却没有合时宜的法令来约束网络上的诽谤行为。今年3月,马亚西亚的TRIPOD.COM网站宣布中止超过20个被认为亲反对党的网页,以阻止他们散布对执政党不利的诽谤性言论。[8]网上传播不是法外地带,所谓的虚拟世界也是现实中的人创造出来的,它也应该接受现实世界的法律调整。然而在不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当政府感到统治威信及地位受到严厉攻击时,打压异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且不论其中的政治因素,上述事情中如果有完善的法律,那些自认被诽谤的人大可站出来采取法律诉讼行动,对簿公堂。暗中中止网站与关闭报馆一样,是过时的专制手段,与将要迈向多媒体发展时代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大马媒体诽谤产生常见的情况
诽谤官司一般是由诉方直接入禀的,法官并不会主动去检查所公布的话语或文字是否构成诽谤。大马最常见的媒体诽谤案常来自报章上的一篇新闻、一篇评论、一幅政治漫画、电视新闻中的某一个画面。在这种情况下,诉方的意愿主宰着是否促成一宗诽谤官司。有些起诉者无理纠缠,明知他们根本不可能胜诉,但他们还是要告,目的是为了骚扰媒体、吓唬媒体工作者,以迫使他们以后休笔、住嘴。有些诽谤性内容不只公布在一家媒体,但诉方在入禀时却只控告某家媒体,按喜好针对性地起诉。比如2000年《太阳报》被前副首相安华起诉诽谤的内容:“指安华是道地的同性恋,道德败坏,不适合担任政府高职”,这些都是引述自首相的谈话,当时多份全国性报章都有报道,惟独《太阳报》一家被起诉。[9]一般情况下,媒体从业人员在本意上并不会愿意自己对被报道、被批评事物的认识与判断和实际情形发生偏离,但在新闻采集至出版、播出整个流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
引发诽谤诉讼的案件,大多是由于媒体从业人员违背了真实性及客观性的原则。真实性与客观性是新闻的生命,但传媒工作者在采集新闻的过程中,往往会受政治环境及各种客观因素影响,运用了主观来判断一件事实的新闻价值。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从1957年独立至今,仍无法摆脱种族主义问题的困扰,各族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时候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当权者在商业上直接掌有主流媒体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例如:新海峡时报集团的80%股权就转入国民企业中,马来前锋报集团亦由执政党巫统(巫人统一联盟)控制,英文《星报》由执政党马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控制,淡米尔报由执政党印度国大党所控制,华文南洋报社也在1993年被前副首相安华的好友郭令灿的丰隆有限公司收购。另外,反对党也各自发行报刊,例如:民主行动党的《火箭报》、回教党的《哈拉卡》、公正党的《公正报》,由于受印刷及出版法令的限制,只能每个月出版两份,不能公开发行给公众人士,却也在近几年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媒体受控于财团或政党的情况下,在新闻报道方面便很难能够独立自主了,也极容易卷入政治漩涡,于是诽谤法令也被搬上政治舞台,我们看到反对党领袖林吉祥起诉《新海峡时报》,也看到了《新海峡时报》起诉《哈拉卡》。无论如何,媒体诽谤发生的原因多是从新闻失实的那一刻开始,不论该媒体集团的“幕后老板”是谁,也不论该媒体的编辑立场倾向,传媒工作者可以尽管选择采用或放弃某一些新闻,但那些把“黑”的说成“白”的行为,绝对是对本身传媒工作者职业操守的侮辱。
除了上述的政治因素,在媒体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里,新闻失真的产生更多的时候是由于为了赶上截稿时间,来不及仔细核查、证实而惹上官司。以华文报业为例,马来西亚人口2500万人,华人500万人,华文报读者190万人,华文报刊要在有限的市场里分一杯羹谈何容易!近年来,数家华文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为了争取读者,纷纷把出版时间提前至傍晚6点出版,这种情况下,采访部都要赶在下午4时截稿,晚报出炉后,又要赶在晚上9点截稿准备印刷日报,华文报馆同时面对传媒工作者流动量大、人手不足的问题,笔者在实习期间就常见记者们驾着车子,以流动电话报告新闻,确保“人未到但新闻先到”;或者看到外国杂志上的精彩报道或评论后,急于翻译给读者,以求“新”、求“独家”来竞争。如果说真、短、快、强、活是新闻写作的要求,其中对新闻要“快”的要求,却很难兼顾“真”(查证)与“强”(内涵),诽谤法令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把媒体作业的难处列为考量之一呢?
三、马来西亚传媒对诽谤诉讼的抗辩及其难处
在诽谤诉讼中,最无辜的是印刷商及出版商,他们也常被看做是传播者而被诉方列为答辩人,一起承担赔偿。在媒体诽谤诉讼中,诉方会首先入禀法院,提出诉讼理由,列出答辩人,申请临时禁令,要求答辩人赔偿、道歉、付堂费、利息。答辩人如果觉得对方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可以向法庭申请撤销诉状;如果法庭驳回撤销申请,答辩人就要准备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尽量把判决的损失降低,这时他可以提出言论属实、合理评论、无意诽谤、道歉、对方允准、特权为自己辩护。
(一)言论属实(JUSTIFICATION)
马来西亚的诽谤法令第8条规定,在诽谤的文字中,对于诉方所做的两个以上的指责,答辩人不须证明每一个指责都是符合事实的,重要的是,那些不能被证明是符合事实的文字应大致上无损于起诉人的声誉,其他的指责是符合事实就行了。[10]
“言论属实”可说是传媒的皇牌,即使是恶意公布的,也不构成诽谤,这时起诉人可说是自取其辱。虽然证明自己的“言论属实”是传媒的皇牌,但是在法律上,所谓的“实”是讲究证据,知悉某些事物为真实,与在法庭上将其证明是截然不同的事。很多时候,只有诉方能接近必要的证据,而可以理解的是,诉方当然不会让辩方太容易去建立其答辩。传媒在充当传声筒的角色时,常引述权威人士的谈话,这些人也常是新闻事实材料和信息的提供者,但是指自己引用别人的谈话还不算事实,还需证实有关事项的真实性。比如政界人士交恶时,A方指B方滥权,有贪污的行为,记者写新闻时如果写出:A方表示,B方滥用职权进行贪污。这就闯下大祸,因为,在法庭上,证明这句话是A方说的还不够,还需拿出证据证明B方真的贪污。除非有关消息提供者能挺身作证,传媒极难证明其真实。依赖这些信息源的后果是,极容易遇上不负责的信息提供者。这需要透明的政治及经济环境,才能为传媒提供收集证据便利,来为自己抗辩。
不过,很多时候事情未到最后都不会水落石出,例如:一些关于商业机构经营出了问题的报道,即使惹来诽谤恐吓或行动,而真相却往往要在最后阶段财政年报表发表时才揭晓,辩方再三复查后确信其报道为真实,即使没有证人,也不宜太早认错,这其实是孤注一掷的做法。
就因为这些举证上的困难,传媒工作者应避免做无法证实之描述,用字选词方面,忌想当然的态度。因此忠于事实的描述及不煽情的标题才是保险的编辑手法。
(二)合理评论(FAIR COMMENT)
诽谤法令第9条规定,所发表的评论必须公平及合理,所表达的必须是意见或看法而不是在强调某种事实。任何评论都必须以正确的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只要基本上正确就可以了。[11]
传媒中的评论人员、自由撰稿人常会对涉及公众利益的课题提出一些评论。这是传媒在诽谤诉讼中最常用的抗辩理由。1997年,《新海峡时报》针对一鸵鸟公司刊登广告号召招资,撰文“养殖鸵鸟必须提供计划书”,被该公司起诉诽谤,法官下判时说:任何有正确知识的人士在未投资前,都会要求进一步投资的详情,辩方发表的文章基于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属公正评论。[12]
“对涉及公众利益的事项的合理评论”是最重要、最常用为抗辩理由的。但常被许多技术性问题阻扰,只要被诉方证明到辩方是恶意的就被推翻了。
“恶意”与否对媒体而言,却是概念模糊的。就算是诉方与辩方之间有私人恩怨,辩方可以说虽然有恩怨,但发表评论是基于公众利益,要揭发原告的不是,不表示恶意诽谤。
(三)无意的诽谤(UNINTENTIONAL DEFAMATION)
诽谤法令第7条规定:若某方在无意的情况下诽谤他人,他可以登报道歉,并补偿对方因诽谤而导致他所花的合理费用,那他可以避免承担进一步的赔偿。[13]
如果诉方接受道歉,则不能再起诉他。如果不接受道歉,无意诽谤对方者也可在诽谤案中以这点作为答辩的理由,进一步抗辩他是无意涉及对方,并且已在报章上道歉,同时他采用有关字眼时是毫无恶意的。广播、电视工作人员常在现场采访,同时在现场立即播放,当他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地播出含诽谤性的言词,几乎在同一时间传送到所有的听众或观众的面前。一个讨论会的主持人,经常可以发觉火辣的言词已经到达构成诽谤的界限,从而设法将其引导入较为安全的境地。但是,再有经验、机智的主持人,也不能完全预防心直口快惹官司的局面。
(四)道歉(APOLOGY)
在诽谤案中,答辩人如果即刻对本身的诽谤性言论道歉,这可以成为减轻赔偿款项的理由。[14]
1998年2月14日,马来西亚前任副首相丹斯里慕沙希淡起诉英文刊物《亚洲新闻》诽谤,一开始,答辩人通过律师致信给予起诉人,否认诽谤诉方,也表示不再刊登类似的被指诽谤性文章。当时的法官驳回了诉方的禁令申请。1999年6月5日,《亚洲新闻》向慕沙无条件道歉,达致庭外和解。答辩人在道歉书中表示:“针对我国所刊登的一篇引述赛胡申谈话的文章,引起混淆的内容导致该文章含有诽谤之意,因此我们愿意道歉……”[15]
在香港,在报刊封面刊登道歉启事为最高格的道歉,笔者认为,受诽谤人士在入禀诉讼前应给予媒体回应、道歉的机会,这样的方式既可以减少社会人士与传媒的冲突,也可避免诽谤为媒体带来的恶性后果。然而媒体面对的多是希望通过诉讼争一口气的人。
(五)对方允准(CONSENT)
这个理由很少可以派上用常如果是对方同意传媒发表诽谤性言论,他当然不可以起诉传媒。不过,如果一个人在公开场合说一些中伤自己的话,不等于同意记者在报上发表,记者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当然,经过同意后诉方又反口,辩方就很难证明这一点,除非有第三者证供或其他客观证据协助,例如:稿件发表前曾由诉方过目,并已将他的意见融入稿件内。
(六)特权(PRIVLLEGED)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传媒工作者做错了事和普通人一样需受法律制裁,传媒的特权是社会人士给予的,因为他代表社会人士采访消息,然后报道给人们,让他们知道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是否得到合理的处置。在一些涉及公众事项的言论中,法律允许传媒在不必负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发表具诽谤性、不真实的言论。也就是说,有关言论享有特权的保护。诽谤法令把特权分为绝对特权(ABSOLUTELY PRIVLLEGED)及有限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D)。传媒可利用特权做为诽谤诉讼的辩护理由。
绝对特权
只有社会利益,才能使诽谤行为正当化,绝对特权是授予与公众利益有关的行为,以确保那些参与公众事务人们的独立与无所恐惧,不会因为冒可能造成的失误负上法律责任而踌躇不前。在马来西亚,享有绝对特权保护的言论范围包括:国会里发表的言论以及国会会议记录,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官、律师、证人所发表的言论,国与国之间高级官员互相来往的信件及谈话,律师与当事人的来往书信与谈话,夫妻之间的来往书信和谈话。[16]。诽谤法令第11(1)条规定,传媒在报道法庭审讯案件的过程享有绝对特权。比如:在报章上公布国会的会议记录、朝野政党相互谩骂的诽谤性言词,报章是不必负责任的。不过,这不代表传媒有权发表任何亵渎神灵的、煽动性的、不正经的、或任何其他被法律禁止的事情。
有限特权(也称有条件特权)
在促进公众利益的大前提下,传媒也许会发表诽谤性和不符合事实的言论,它不一定要负法律责任,赔偿诉方。但它发表言论时必须是出于善意,不含不良企图。特别是对媒体而言,藉此特权报道政府施政及部分公司机构活动的利益,是社会大众监督政府活动及对普遍影响社会大众生活事物的资讯之合法需求,可见这项特权所保护的范围并不是刻板的,不同的法官是会随着不同的社会环境来定义。有限特权的范围包括:国会会议中(不同党派人士的言论)的公平及正面报道,在执行法律上、社会责任上、或道义责任时所发表的言论,维护本身的合法利益时所发表的言论。1999年2月26日,前副首相安华起诉英文报章《太阳报》诽谤,该报在入禀答辩书时提出的辩护理由就利用了此特权:它拥有“有条件特权”,同时基于道德和社会责任进行上述报道。而且这篇中肯及准确的报道是根据首相在记者会上作出的,读者有合法的利益接受有关信息。[17]答辩方也说,首相的谈话是假设安华涉及鸡奸行为,这些假设案情涉及公众利益,在不含恶意的情况下,不论有关案情是否正确,它报道假设的案情是受到保护的。
上述特权是法律保障媒体言论自由的具体体现,它们似乎是传媒头上的一道保护光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特权所给予的保护范围还是有欠宽广。最明显的是,它仅保护公开会议的报道,而实际上一些政党或商业机构的内部会议会有更多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内幕,然而,大马传媒并没有报道权。即使是公开会议的报道,也有可能被指与公众无关。笔者在实习过程中,遇见一些受访者受访时透露一些内幕,可是采访后却被对方告知“这个不要写,那个不能写”。另外,在报道地区、国内或国际政治人物时,只要媒体在每个阶段都是合理的,就该享有特权。
四、诽谤诉讼对马来西亚传媒的影响
近代世界各国司法界对诽谤的法律原则未尽相同,然而随着民主政治兴旺及媒体的发展,不断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诽谤法令与言论自由的冲突。
与各国一样,在努力地维护个人声誉的同时,诽谤法令直接地与马来西亚宪法第10(1)(a)条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力发生矛盾冲突。多数学者在法理上反对赋予新闻媒体超乎一般民众个人自由权利之上的制度性特权。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及律师公会会长也先后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诽谤他人的准证。
大马对传媒的诽谤诉讼是近年来媒体的热点。且不论诽谤官司背后可能藏有的“隐议程”,一场诽谤诉讼里面,胜了要还诉讼费、堂费,败了还要偿还高额赔款,即使是庭外和解,也都必须以不曾公布的数额解决。1997年的方木山对太阳媒体集团、米占马哈迪对三家华文报都是以不曾公布的数额庭外和解。虽然大马传媒的诽谤诉讼“案龄”尚浅,由于传媒须为诽谤官司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诽谤官司带给媒体无形的压力。
大马传媒言论自由再受威胁
今年,律师公会成立了诽谤案的言论自由影响报告委员会,拟了一份报告书呈交给东马(马来西亚在婆罗洲的两个州属)、西马(马来半岛)两地的首席法官及首相署部长,报告书中提出巨额赔偿对于宪法下言论自由及世界人权造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影响,报告书也呼吁有关部门进行司法改革。[18]首相署部长莱士雅丁在今年4月13日表示年杪将提诽谤修正案,高额索赔诽谤案料将成绝响。[19]
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永远是新闻理论不老的话题。要问大马传媒有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绝不会有人斩钉截铁地说“有!”。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应达到的理想目标是免受政府与实力团体的干预,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政府单位有权决定新闻机构该发表什么消息,可不可以报道什么事件,一旦政府掌握了权利,新闻的自由自主权就丧失,也是独裁的开始。
大马宪法虽然列明,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随后而至的法律限制还包括:1948年煽动法令、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1967年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法令、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在这些法令下,内政部给报馆打电话是平常事,官方对新闻的打压自不在话下,法令只是发挥压制言论自由的作用,真正发挥长期对媒体言论的操纵,却是执政党在商业上直接掌有的媒介所有权和控制权。大马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以后沿用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政治体系,表面上实行三权分立,媒体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第四权。但由于执政党在国会的议席超过了三分之二,掌握了立法权,由他们的国会议员组成的内阁,掌握了行政权,在1988年修正宪法时,把法庭置于联邦法律下,从此法庭属于行政机构,四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架构基本上已经彻底瓦解。
诽谤法令以高姿态出现后,传媒为了避免惹上官司,常不自觉地对自我采取打压的自律方式。传媒在平常作业中无不步步为营,显然,高额索赔的诽谤官司,无疑的对于马来西亚传媒而言可说是雪上加霜。1994年之前,诽谤案最多是20万零吉(约人民币40万元)的索偿。在1994年法庭判《马来西亚工业杂志》需对诽谤商人陈志远赔偿1千万零吉(约人民币2千万元),数名答辩人较后入禀上诉,要求联邦法院撤销裁决,但皆被驳回。这为马来西亚诽谤案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在大马,媒体工作者如新闻记者、评论撰稿人、自由撰稿人等,一般都不属于高收入者,要他们个别做出赔偿,可能面对破产的命运,届时其个人及家庭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如果是媒体机构,对一些财力雄厚的媒体机构而言,一千万的诽谤赔偿已经是勉强的支出,然而对一家依靠炒作新闻吸引读者的小报或杂志而言,可使他们陷入财政支出的困境。笔者与一些报界前辈交谈时就听说,诽谤法令似乎在间接帮助政府牵制言论自由,把控制言论自由的权利交给了普通人。
社评作者也注意到:“那些过去‘身心都受到严重创伤’的传媒,却在这个时候异常沉默,没有多少回应,甚至连应酬的文章和评论也不见。到底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身心俱疲无心再讲?”。[20]大马媒体发展史上,对媒体言论自由的打击,1987年的“茅草行动”[21]可说是最严重的一次,许多政治评论作家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入狱,英文《星报》、华文《星洲日报》、《祖国报》也被吊销出版准证。
当然,一个人的声誉也是宪法所保障的人身自由,在一个没有明确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维持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均衡的难处,也是维持社会责任和新闻自由之间的难处,新闻自由过于被强调,容易变成极端自由的媒体,但如果社会责任高压于新闻自由之上,极可能变成畸形、专制的媒体。
律师公会前任主席苏莱曼阿都拉曾表示,法庭判决巨额赔款,可能会导致新闻媒介不敢再揭露对人民、环境、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的种种活动或计划。[22]他也说,如果法庭根据以往的庞大巨额赔偿的案例判案,最终只会令人们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失去信心,并且也对“诽谤”起诉产生恐惧的感觉。[23]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人物、企业、经济、社会及其他公众生活圈子的掌权者,都应该接受公众及媒体的批评、指责,公共事务需要大家辩论,这种辩论该是公开的、激烈的,辩论者的言论难免有失误之处,这种失误是正常的,如果一讲错误就被告诽谤,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参加辩论了。
新闻作业空间无法伸展
如果在诽谤官司中败诉,传媒须付出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堂费及利息。这些费用在账目里可视为“可估计风险”(CALCULATED RISK),将提高媒体的营运成本。但媒体的营运成本提高,不能随便加之于消费者身上,于是往往从内部削减开支,削减员工福利。“1994年陈志远案”中的一千万赔偿,如果换成是派记者出国采访的开支,对于记者本身及读者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吗?
诽谤法令令传媒工作者为了避免闯祸,遇到可能有诽谤性的报道时,首先用“凡是有可疑点,不用”的标准来衡量稿件的价值,不去找或来不及找法律意见,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形成了自我审查的恶性循环,将大大地削弱媒体机构的竞争能力,因为其他媒体机构可能掌握同一件事物的真实性而抢先发布,这也间接地剥夺了受众的知情权。受众难以看到有爆炸性的、深入的内幕报道,也绝少看到有关富商名人的负面报道,却不时看到一些针对刑事案疑犯、伦理悲剧主角、娱乐圈人物的揣测性的报道。
为了避免官司,有些记者往往采用扭曲的侧面报道手法,以求把打听到的片面消息透露给读者。评论作者则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转弯抹角、语带双关地在字里行间传达有贬意的讯息。1998年大马政治动荡期间,《星洲日报》评论作家曾毓林就用西游记的主角来影射政坛领袖。《南洋商报》资深报人在其时评专栏《见虎烧香》中也运用这种写法。虽然能吸引许多爱探内幕的读者,殊不知这种做法极容易触犯法律。其实这种做法与大马畸形的传播环境有关,传媒工作者常常都苦于“有话不能直说”,才会在文章中把想写的东西东躲西藏,笔者认为由于写法过于轻佻,长远来说,将令传媒机构无法建立起令人尊敬和信任的形象。
促使传媒恪守新闻原则
我们说新闻的真实性及客观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每一天的新闻报道,在将来都会变成历史学者重要的资料文献来源,今天失实的新闻,也会造成日后历史记录失实。前面分析了诽谤产生的原因也大多是偏离了这两个原则。做为负责的传媒,不该凭空想像、随意歪曲事实、恶意地去诋毁别人。诽谤法令在积极的意义上,能使传媒提高自己的道德操守,在进行新闻报道、评论、摄影、录音、录影、编辑、创作漫画等传播工作时,都能用心处理,确保自己所发表的言论的可信度。
香港人口600万,却养活了数十张报纸,还有数不清的周刊、月刊和各类型刊物,加上数家有线、无线电视台、电台。与之相比,大马虽然有2千万人口,但多元种族文化环境、多元语文教育环境使媒体事业面对着读者市场细分化的问题。比如,华族占全国人口的
23%,大部分接受华文教育的华族在选择阅读刊物时,往往以华文刊物为首选,华文报刊读者自然较英文、马来文报刊少,广告收入自然减少。要留住读者,只有不断地鞭策自己恪守新闻原则,提高新闻素质,才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大马两大华文报就分别定下了它们的严肃办报宗旨:《南洋商报》为“公信第一,关爱常在”,《星洲日报》为“正义至上,情在人间”。
1957年诽谤法令纵有不合时宜之处,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那些因自己的声誉受毁的人士所采取的法律行动,也可说是其中一种受众的反溃这样的反馈未免苛刻,却也可无时无刻地提醒传媒工作者,注重新闻的查证工作,通过严谨的新闻操守避免带给自己和别人不必要的麻烦。
结论
马来西亚的媒体工作者不易为。媒体机构常被迫在公众利益与媒体机构的私人利益之间做抉择。现有的诽谤法令尚无法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传媒像头戴紧箍圈走在钢索上,只能在法令下战战兢兢地运作,苟延残喘。
综上所述,大马传媒必须力争司法及立法方面的改革,也还需依靠传媒本身的自律,二者相辅相成之下,才能在尊重人身自由与维护本身的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点。
注释
[1]杨培根:《诽谤法令知多少?》,《星洲日报》1998年6月11日。
[2]《星洲日报》2000年8月24日。
[3]《律师公会诽谤法令对言论自由影响报告》,《南洋商报》2001年4月8日,《南洋论坛》封面版。
[4]《星洲日报》2000年8月24日。
[5]《律师公会诽谤法令对言论自由影响报告》。
[6]Keiths R Evans,The Law of Defam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Butterworths,1993年版,135页。
[7]陈华芝:《罪名比赔重要》,《南洋商报》2001年3月24日,第2版。
[8]《南洋商报》2001年3月21日,第20版。
[9]《南洋商报》1999年7月2日。
[10]Defamation ACT 1957,1993,International Law Book Services,[BF]P.4.[BFQ]
[11]Defamation ACT 1957,1993,International Law Book Services,[BF]P.5.[BFQ][12]《南洋商报》1999年6月3日。
[13]Defamation ACT 1957,1993,International Law Book Services,[BF]P.2.[BFQ]
[14]杨培根:《诽谤法令知多少?》,《星洲日报》1998年6月11日。
[15]《南洋商报》1999年1月6日。
[16]杨培根:《诽谤法令知多少?》,《星洲日报》1998年6月11日。
[17]《南洋商报》1999年7月2日。
[18]《南洋商报》2001年3月16日,第12版。
[19]《南洋商报》2001年4月4日,第9版。
[20]陈华芝:《罪名比赔重要》,《南洋商报》2001年3月24日,第2版。
[21]1987年教育部委派不懂华语的华人到华小任职,华社一致表示反对,三大华人政党和十五华团在吉隆坡天后宫大集会以商对策。10月27日,国阵政府内政部发出连串逮捕指令和行动。
[22]《南洋商报》2001年3月16日,第12版。
[23]《南洋商报》2001年3月16日,第12版。
参考书目
Defamation Act 1957,International Law Book Servieces.
The Law of Defam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Keith R Evans,Butterworths.
Power Publicity and the Abuse of Lible Law ,Donald M Gillmo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bel and Slander,Peter F Carter Ruck & Harvey Starte,Butterwor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