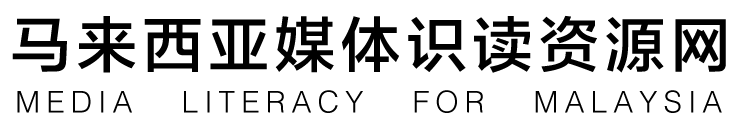2015.01.15【燧火评论】《查理周刊》惨剧的第十三个牺牲者
【庄迪澎】充满灾难的2014年结束,许多人期许2015年告别阴霾之夙愿显然事与愿违。1月7日法国发生穆斯林枪手闯入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办公室,血腥屠杀编辑、漫画作者和警察共12人;8日和9日再先后发生枪杀女警和枪手攻击犹太人超市事件。由于《查理周刊》遇袭疑因早前曾发表讽刺伊斯兰国(ISIS)头目巴格达迪的漫画而遭报复,法国人发起「我是查理」的集会,以示捍卫言论自由。
《查理周刊》惨剧令人想起25年前的《魔鬼的诗篇》(The Satanic Verses)事件。英籍印裔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在1988年9月出版了这本以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招致当时的伊朗精神领袖科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0-1989)在1989年2月对他下达全球追杀令,据传赏金甚至高达三百万美元。不同的是,由于得到英国政府保护,以及伊朗政府在1998年宣佈不支持追杀令以便与英国恢复邦交,鲁西迪保住了小命,还能风骚地在2001年的英国电影《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裡客串演出(虽然鲁西迪没事,但据报导,有些国家的《魔鬼的诗篇》译者和出版人曾遇袭伤亡)。
同样是「冒犯」伊斯兰和穆斯林,身处在恐怖主义袭击猖獗时代中的《查理周刊》就没这麽幸运了。主角的命运虽不同,桉情却一样:一边创作了「冒犯」伊斯兰/穆斯林的内容(小说/漫画),另一边觉得被「冒犯」,而採取「处决」冒犯者的手段反击。在崇尚言论自由作为宪赋权利的民主国家,「因言获罪」肯定违反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更别说偏离法律途径而以私刑致死言论冒犯者。所以,《查理周刊》惨剧发生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均以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谴责凶徒,以「我是查理」运动来彰显捍卫此价值之决心,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自由」是这个社会所珍视的价值。
言论自由的绝对与相对
然而,捍卫言论自由的说法也不无争议,法国也有较少数的民众发起「我不是查理」运动,宣示反对侮辱宗教的立场。一些亚洲国家的官员、从政者、新闻从业员乃至学者,亦祭出「言论自由非绝对」之类的观点申论《查理周刊》惨剧,虽然还不至于幸灾乐祸,但颇有《查理周刊》咎由自取的含意。在距离法国一万公里的马来西亚,媒体应否享有冒犯宗教的言论/新闻自由,也成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交锋的课题。
《查理周刊》惨剧所衍生的这些争议,其实也展示了一种「言论自由的政治」。不论喜欢与否,对合法政府而言,谴责恐怖袭击是一种政治正确,即便是威权治国,在国际上还是得发表这种外交辞令。然而,「提醒」和「重申」言论自由「并非绝对」,对威权政府而言同样是政治正确的必要举措,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方可合理化在国内限缩公民的自由空间与民主权利。而且,当这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有新闻工作者、从政者和学者也以「言论自由非绝对」来申论此事时,我们大抵可以知道,这种经过长期熏陶的官方论述何其成功。
「言论自由非绝对」此一说法确实说出了一个「事实」--全球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民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即便是有《宪法第一修正桉》禁止政府立法管制新闻自由的美国,亦有诽谤法约束言论诋毁他人;作为「亚洲民主典范」的台湾亦有诽谤罪--最近马英九总统就向指责他收受二亿台币政治献金的媒体人周玉蔻提出诽谤告诉。现实是,「自由」只有不断追求更好的状态,别天真地以为有「圆满」或「绝对」的状态。所以,正是因为这个「事实」,「言论自由非绝对」的说法也根本就是一种伪命题,因为即便是「受到限制的言论自由」,假使确实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吾人均需承担自由的代价。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这个代价,或我们以什么态度承担这个代价?假使我们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即便摆在眼前的仅是「有限制的言论自由/非绝对的言论自由」,难道也是靠枪杆子来解决掉当中某些「冒犯」我们的言行?
这点也许就是自由国度与威权国度甚至恐怖主义的不同。吾人需要承担的自由的代价,就是自由会带来多元,不论是政治主张、艺术、音乐、文化,有精緻、有低级、有优雅、有粗俗、有悦耳、有刺耳、有讚美、有非议、有恭维、有调侃。我们不可能都喜欢,而他人同样也不可能都喜欢我们的声音,但自由的价值在于,大家共同尊重一套游戏规则,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不满意和解决争端,而非诉诸暴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国家的政府首长,即便民意基础再高、人气再旺,也概况承受对他们的批评、攻击,甚至嘲讽和恶搞,而不是诉诸文字狱,更别说以暴力消音。
《查理周刊》惨剧本身更是印证了上述差异。《查理周刊》创刊于1970年,虽说历史悠久,但在法国还说不上是全国瞩目的刊物,更别说全球。发生惨剧之前,恐怕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份刊物,惨剧后,或许会以刻板印象认定《查理周刊》又是一份典型以基督教文明为尊、藐视伊斯兰的「西方媒体」。然而,据报导,过去曾遭《查理周刊》恶搞的对象包括使罗马教宗、红衣主教团、圣母玛利亚、王室,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等从政者,并非专门针对伊斯兰的所谓「西方媒体」。这些「被冒犯」的「西方宗教」和「西方政客」,并没有向《查理周刊》发动暴力袭击。崇尚民主与自由的人,也许就应具有某种自我解嘲的能力与自信来面对异议者的「冒犯」。
恐怖袭击践踏言论自由
前述以「言论自由非绝对」来议论《查理周刊》惨剧的立论之所以颇有指责该刊物咎由自取的含意,是因为认为该刊物「冒犯」他人在先,就得承担代价。这种「做错事,负责任」的思维,看似没错,但问题在于:一、谁有权代表伊斯兰社会界定怎样的内容已经踩到了「冒犯」的底线?二、即便我们都原意接受《查理周刊》犯错这个前提,又是谁有权代表伊斯兰社会来决定应该对他们处以极刑?
《查理周刊》惨剧不仅伤害了言论自由,甚至是超越言论自由这个范畴。吾人不应将它当做仅仅是攸关打压言论自由的孤立事件,而是应该将它放在近年甚至是近日的恐怖主义的脉络裡--法国一连三天的枪击事件后,1月10日,尼日利亚和黎巴嫩都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30死55伤。若说《查理周刊》惨剧的死者是咎由自取,为「肆无忌惮的言论自由」付出代价,那麽在一连串恐怖袭击中丢了性命的百姓又何罪?恐怖分子所为,已非他人言论是否合意的问题而已,而是「非我族类」几乎都可以成为他们草芥人命的对象。
逢有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团体总会尝试划清界线,严正声明正统的伊斯兰并不主张恐怖主义。此举无可厚非,但不主张恐怖主义的说法,应该贯彻始终;以「冒犯」的说辞来暗示《查理周刊》咎由自取,恰恰是不自觉地沦为恐怖主义的同情者和辩护士,即便言辞间仍是信誓旦旦对辩称伊斯兰恐怖主义不等同于伊斯兰。
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有一套解释伊斯兰恐怖主义崛起的理论颇有市场,就是认为西方强权主宰全球资讯平台和沟通管道,造成日益边缘化甚至遭压制的伊斯兰少数声音不得不诉诸恐怖主义手段,以便世界听见他们的声音。就国际权力结构之现实而言,此观察和解释未必完全不可取,但不应成为「谅解」恐怖主义的凭据,否则这种弱势者人人皆可施暴、强势者人人得而诛之的主张成为王道,世界大乱必不可免。
恐怖主义之「恐怖」,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构成「冒犯」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要素有哪些、界线有多小。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会遭枪手冲进办公室或住家乱枪处决、不知道哪一天在菜市场买菜突然被炸个粉身碎骨,或是哪个时间在咖啡馆喝咖啡会瞬间变成蜜蜂窝。曾在2005年刊登穆罕默德漫画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在《查理周刊》惨剧发生后的两天发表社评说,该报过去九年活在恐袭阴霾下,为安全起见不再转载《查理周刊》的漫画,说明瞭这种恐惧(fear)立竿见影。
《查理周刊》惨剧死了十二个人,却有十三个牺牲者。 ‖ 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