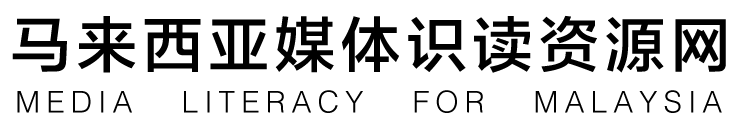2005.11.19【独立新闻在线•寒蝉有声专栏】“粉丝”与公民不能一刀切
【庄迪澎】中文电台“哗!FM”在10月15日停播,转眼间已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停播前,听众踊跃扣应哽咽声援、万人网上连署、三百人共赴停播前夕的告别烛光会,以及媒体跟进报道,令“哗!FM”停播事件成为九月至十月期间其中一个热门华社新闻。不过,有论者质疑“哗!FM”停播事件何德何能得到公众及媒体这番眷顾;也有论者对公众声援“哗!FM”的行动不以为然。
前天(11月17日),《东方日报》刊出潘永强的专栏文章《粉丝社会还是公民社会?》,文中对人们声援“哗!FM”颇不以为然,直陈声援“哗!FM”的公众只是“粉丝”(fans),而“粉丝”并无坚定和持久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因此不要把“粉丝”误以为是“公民”。
潘永强也附和能源、水务与多媒体部长林敬益的话“即使百万人签名也挽救不了”,因为林敬益“清楚市场、法律与政治的界限,没有干预市场与商业运作”;并质问“公民社会不是要求国家减少干预,为何一出问题就回头找国家插手?”
一家媒体公司开张营业、易手、清盘,一般是商业考量的结果;“哗!FM”停播与ntv7债务重组及首要媒体有限公司收购ntv7这些商业动作不无关系,但是如果因为“哗!FM”停播是媒体企业基于损益考量而作的决定,没有外露的政治介入或压力,便将它看成“仅仅”是商业事件,无关政治、无关言论自由之利害,则未免见树不见林,忽视了媒体业与现代政治社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从媒体属性来看,相对于报纸,广电媒体如电视、无线电广播(电台)及电影的娱乐性质较强,因为广电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阅听人的视觉与听觉享受。再加上阅听人不需要有很高的识字能力,也能享受广电媒体的服务,因此,广电媒体往往比印刷媒体更受欢迎、更普及。
不能总是庸俗化大众
马来西亚的电台节目主要也是以音乐及流行讯息挂帅,由于音乐节目和流行讯息往往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碰触政治、社会议题,是属于“安全”地带,因此人们也鲜少将“言论自由”这个概念和电台节目联想在一起。“哗!FM”固然也和其他电台一样,音乐与流行讯息仍是主要成份,但是在“哗!FM”停播事件中,却有两个相对不寻常的现象值得观察,也应该成为评论“哗!FM”停播事件必须考虑在内的因素:
一、声援“哗!FM”的听众并不是因为从此少了一个听歌及洞悉偶像动向的频道而扼腕惋惜,而是不甘于“下班红绿灯”这个卖言论、让许多普罗大众扣应畅谈的节目即将寿终正寝。
二、潘永强所指的“几位刚冒出的节目主持人”,都称不上是中文广播界里的当红DJ,他们却能令人们“热血沸腾”。为何潘永强所谓的“粉丝”推崇的并不是那些凭油嘴滑舌主持嬉笑胡闹节目的当红DJ,而是卖言论节目的“菜鸟”?
这两个现象告诉我们几个讯息:
一、他们即使是“粉丝”,也是对言论空间有所求的“粉丝”,未必如潘永强所认识的那类对公共事务白痴的追星族“粉丝”。将这类所谓“粉丝”和看到周杰伦便会尖叫的“粉丝”归为同类,把“粉丝”与“公民”一刀切开,未免草率。即使知识份子也可能是某个大师的“粉丝”,就如有些知识份子会自命为主张“介入”的爱德华赛依德(Edward Said)的“粉丝”,虽然这些人当中有些总是自命清高地将自己和政治活动划清界限。
知识份子不能总以空想理论家的视角、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像过往封建贵族社会自命清高地认定“大众”(mass)就是低层次的乌合之众,非得庸俗化“大众”,判定大众不成熟、不懂事、不会思考,一定是热血有余、理性贫瘠。否则这和政府经常抬出“人民不成熟”的论点合理化对言论自由的箝制,有何不同?
二、“哗!FM”现象反映了广播业已经起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从前,我们扭开电台频道,除了歌曲、广告,就是DJ空洞苍白、莫名其妙的对话,或嘻嘻哈哈胡闹,听众除了转台之外,就只是投书报社发发牢骚而已。电台管理人仍然对“卖言论”这类“硬”的时事节目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这类节目没有市场。“哗!FM”现象说明了电台听众不但不排斥“卖言论”的节目,还非常支持。这对“引诱”媒体同业制作更多类似节目,进而营造公众勇于发言的氛围,有其积极意义。“Ai FM”及“988”这两家中文电台和先后制作类似“下班红绿灯”的节目,就是实例。
我们不能假设“哗!FM”的听众都是同类人,正如我们不能假设“粉丝”都一定是只有热血沸腾而无思考能力之人。人类本来就有不同利益、不同旨趣;现代政治社会里的利益团体和压力集团,也都追求个别不同的利益。不同路的人马也许结盟也许不,而且不同的利益群体得到支持响应的程度也各异;有些人特别重视环境问题,有些人关切民权问题,而环境问题也许会因其政治色彩相对淡薄而吸引许多避忌涉足政治活动的人连署声援,以致其所“展现”的力量要比动员“废除内安法令”的运动来得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判定热衷于非政治运动的社群,就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
公民社会总要经历始于足下的阶段
社会/政治运动的力量之规模,以及其关怀重点,不必然就是区分何者是公民、何者不是公民的标准。政府兴建吉隆坡-布城大道,由于规划不当,以致在吉隆坡大城堡的高架公路路段距离民宅只有咫尺之遥,当地居民自发性启动抗争机制,架设网站、到国会大厦拉布条迫使工程部长三美威鲁走出来对话等等。社区居民拉布条抗议,大城堡居民不是先行者,有细心观察马来西亚社会变化的知识份子应该都能注意到,最近几年来,这类活动越来越普遍,人们比以前勇敢多了。
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究竟是否成形?如果已然成形,是强是弱?学界固然看法不一。但是,将大城堡居民或其他社群居民的抗争,以及公众声援“哗!FM”的现象摆在马来西亚国情脉络里看,我们应该承认这类运动在公民社会的产生/成形/勃兴过程中,所昭示的意义。
虽然有上万人上网连署声援“哗!FM”,但是“哗!FM”停播前夕的烛光晚会仅有大约三百人到场。在我看来,三百人仅是很小的人数,但在马来西亚国情脉络里从阅听人本质来看,它仍然可产生“星星之火”的积极意义。公民社会的活力的勃兴,有赖于个人与社群相互学习和壮胆,总是有小撮人当了先行者,给后来者壮胆、把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变成家常便饭活动,才可能感召更多的人、壮大公民社会的队伍。
传播学研究经常发现阅听人被动、消极,我向来认为,马来西亚的媒体阅听人尤其如此。多年来,阅听人对报纸、电视、电台的内容优劣,即使有认识,而且也未必没有感受,但少有主动向媒体抗议。马来西亚媒体阅听人的消极被动,与公众对攸关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逆来顺受的性格,基本雷同。不过,最近几年来,社会气氛和公众个性的确起了变化,有人愿意走出来,就是一个进步。公民社会之兴起也要经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阶段。
易言之,走出来声援“哗!FM”的听众,愿意公开表达自己希望保留“哗!FM”,进而保住“哗!下班红绿灯”这个卖言论的节目,不怕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印在请愿书上交给政府部门,相对于阅听人和群众历来的沉默、消极、被动,它实实在在反映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他们的努力有没有成果、他们有没有参与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那已是另一回事了。
“哗!FM”事件延伸三个议题
“哗!FM”停播固然不是外显的政治势力打压的结果,但将它解读成仅仅是“商业决策,与人无由”,视野未免狭隘。“哗!FM”停播事件至少延伸、凸显了三个攸关媒体业与公共利益的议题:
一、我国广电媒体业不像报业那样,有所谓的“中文”报业;所有电视台都是非中文机构,而电视台旗下的中文节目及经营广播的子公司,都只是这些媒体机构里可有可无的附属单位。“哗!FM”停播事件凸显了中文电视/电台的“二奶命”现象,而这是关乎非主流社群接近使用媒体的权利的议题。
二、“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提出“检视广电政策,推动公共广电媒体”的主张,又是“哗!FM”停播事件延伸出来、值得思考和探索前景如何的议题,甚至是可经营努力的新方向。
三、将“哗!FM”停播仅仅解读成“只是商业运作”及“市场逻辑”的结果,群众声援“哗!FM”是“流错泪”,只是向大行其道的商品逻辑俯首称臣,弃械投降。资本家作如此想,并不稀奇,但是知识人和评论人也如此主张,则未免令人失望。倘若市场逻辑非得是决定市场有什么、没有什么的唯一和至高无上的标准,则人类社会终究会丧失许许多多不能也不应该以市场逻辑和金钱利益衡量的事物。就媒体与舆论多元性意义而言,如果按照市场逻辑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媒体与舆论同质化必将积重难返,而我们根本不需要感叹马来西亚养不起像样、能永续经营的政论杂志或异见媒体,因为市场逻辑已经决定了这类媒体的命运,大家还吵什么?
由此申论,促请国家/政府检视广电政策,推动公共广电媒体的主张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但是推动媒体政策的转变,以及游说国家机关/政府出资建立像英国广播机构(BBC)那样的公共广电媒体,诉诸对象肯定是国家,因为唯有国家立法及分配资源,创建公共广电媒体的夙愿才可能实现。如此一来,要“国家插手”在所难免。
“国家插手”也能保障公共利益
利益团体或公众要求“国家插手”保卫“哗!FM”,不一定不妥,问题在于国家插手的动机为何?国家如何插手?国家插手的结果为何?
在马来西亚,国家机关的确是打压新闻自由的合法暴力集团,但是国家机关的职能原来并不止限于此。国家机关其实可以发挥保障新闻自由与多元舆论的作用。
我固然极力反对国家机关强权打压公民社会的自主性,但是除非你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否则你无法全然否定现代国家具有保护公共利益的职能,例如维持治安、建立有利群众的公共医疗系统、立法保护历史建筑物、立法保障弱势群体等诉求,都是国家应该行使、可以行使的职能。政治学意义中的利益团体和压力集团,他们诉诸的对象,不也是国家吗?
就媒体业与新闻自由而言,国家介入不一定只能干预言论空间、打压新闻自由;国家介入可以是保护舆论多元性,例如美国制订的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可以避免媒体由单一集团垄断,保障多元舆论、英国立法设立英国广播机构,以及国家分配大气电波,也能保障大气电波不被财雄势大、掌握先进技术的集团掠夺垄断。诉诸国家插手,短期可以经由行政命令权宜性改善不正常现象,长期可以促成立法或制订政策修正不正常现象。 ‖ 原文出处 ‖ 下载PDF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