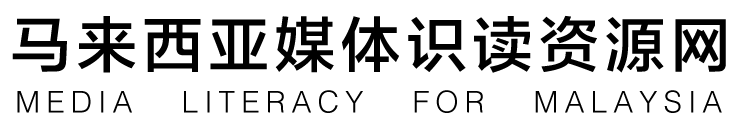2012.04.14【东方日报•名家】莱纳斯广告、律师信与言论自由――传媒论衡(五)
【庄迪澎】今年3月13日,世华媒体集团旗下三份报纸刊登澳洲稀土公司莱纳斯的“报道式广告”(advertorial)而引发争议时,《星洲日报》的“官方面子书”硝烟四起,一些护主的中阶主管乐此不疲地和读者对呛,甚至有人搁重话,仿效马哈迪在2000年苛责“华团大选诉求犹如共产党”那样,反呛读者“只是因为我们认为人家讲的话是错误的,就不给人家讲话(打广告),那跟共产极权的作为有何区别呢?”
《星洲日报》“封杀”批评者早已恶名昭彰,其中阶主管竟以大义凛然的姿态苛责读者“打压言论自”,固然煞是讽刺,但值得吾人思考的问题是:读者批评报社刊登莱纳斯的广告,甚至主张拒收莱纳斯的广告,说得上是“打压言论自由”吗?何其有趣的是,4月7日传出,莱纳斯发律师信恫言起诉联署敦促首相纳吉撤销莱纳斯稀土厂临时操作执照的45个非政府组织;两相对照,一并讨论,何者“打压言论自由”,不言而喻了。
“打压言论自由”是国阵威权统治的常态,“你们打压言论自由”这类呐喊亦频密出现,是也喊,不是也喊;很多不学无术的政客,甚至媒体工作者,在他们的言论遭读者尖锐批评却无法自圆其说时,就动辄申诉对方打压他们的言论自由。《星洲日报》的中阶主管在面子书以此回呛读者不留情面的批评,徒添另一例证而已。
这里牵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何种作为才说得上是“打压言论自由”?二、广告是否属于应受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
首先,“打压”必然涉及行使某种程度的暴力(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暴力),而且在“打压者”和“被打压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中,“打压者”比“被打压者”占有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
缺乏权力、资源何来打压?
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执政党动辄诉诸法律行动(例如援引内安法令、煽动法令、诽谤法令)逮捕、起诉揭露和批评政府丑闻的异议分子,甚至将他们定罪,不仅是诉诸合法暴力剥夺异议分子的言论自由,又能起杀鸡儆猴之效,阻吓其他潜在的批评者噤声。至于非法暴力,包括政治暗杀,或是在非政治场域,某甲因不满某乙的言论,而纠众痛殴甚至杀害某乙。
无论是行使合法暴力或非法暴力以消除“逆耳”言论,无疑都是“打压言论自由”;而且,只有当“打压者”掌握相对优势的权力位置,始有可能使“打压”举措产生效果,进而成为“打压者”――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无权无势者有能力使他人屈从于自己吗?
相对于为莱纳斯设厂大开方便之门的国阵政府、财雄势大的莱纳斯,以及拥有百万读者且年赚上亿的世华媒体集团,反对莱纳斯在马设厂的读者,乃散居各地、没有组织、缺乏资源的个体,既无让报社一夜之间关门大吉之权力,亦无掌握能使刊登不实广告者成为阶下囚的合法暴力;在不具备构成“打压”行为的必要条件之下,何以构成“打压言论自由”之事实?
反之,反对莱纳斯在马设厂的读者在《星洲日报》面子书里留言批评,恰恰是尊重批评对象的言论自由,认定对方有答复的权利、自由、机会和义务,并且期待与对方论见相订。报社里全职从事文字撰述工作的职员比比皆是,亦有使用面子书和报纸版位回应读者诘问的便利和优势;不幸的是,《星洲日报》未能展现从容应对读者诘问的谦卑态度,反而任由诸如陈莉莉这等资深职员以“一堆粪青”(不是愤青)、“和他们这些不懂媒体的人讲新闻,真浪费时间”等傲慢言论回呛读者。胸襟之小、思维之浅,委实中文报业的悲哀。
敦促媒体负责也不对?
诚如我在2011年8月15日发表的《抵制媒体,是阅听人权益――新闻自由论衡(四)》一文里指出,媒体产生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y)牵连层面深而广,即使没参与其中的人亦受牵连,因此包括读者在内的公众都是媒体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莱纳斯在马设厂的潜在“毒害”,乃攸关全国人民安危的公共事务,倘若其仗着雄厚资金发动媒体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淹没反对之声,并使得设厂计划通行无阻,以致在可见的未来重蹈1980年代霹雳州红泥山亚洲稀土厂造成的灾难和悲剧,媒体刊登莱纳斯广告业已产生了足以牵连全民的负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可谓为帮凶。
职是之故,读者批评《星洲日报》对莱纳斯广告来者不拒,甚至敦促这家广告业绩早已丰收饱满的报社拒收莱纳斯广告,乃自觉地承担监督媒体的责任,既是维护自身权益,也是维护整体社会的福祉。报社当然有权选择要对民意从善如流,还是向广告金主鞠躬磕头,但它们不能否决读者对其决定做出相应行动的权利。倘若报社选择与民意背反,它就得承担作此决定所招致的后果,例如读者罢买以示抗议。
至于第二个问题,已被普遍认定的“言论自由”的保障对象,是公民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是企业行号刊登的商业广告。社会运动提出诉求之公益广告,亦应享有言论自由;但是,企业行号阐述生产活动的商业广告,少有(即使不是完全没有)被认定为属于“言论自由”保障之范畴。
检索国际维权组织评定各国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状况的标准,吾人何时看到它们把商业广告列为观察对象;吾人又何时看到它们把媒体阅听人对媒体的监督、批评乃至杯葛,视为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威胁?
话说从头,莱纳斯发律师信限定“拯救马来西亚,中止莱纳斯”委员会(SMSL)等45个非政府组织在七天内登报道歉及撤销公开信,否则将提起诽谤诉讼,这种意图助司法机关之力迫使“异议”从舆论市场中消失之举措,恰恰是“打压言论自由”的其中一种典型手段。除非吾人无视我国公权力随时为政客所用、司法独立不彰,且1990年代以降频密出现以“巨额诽谤诉讼”(mega suits)作为“消音”手段之事实,否则焉能漠视莱纳斯诉诸诽谤诉讼乃“打压言论自由”的可恶行径?
读者仅是在面子书上留言批评,尚且被质疑“跟共产极权的作为有何区别”,莱纳斯意图对公民团体诉诸诽谤诉讼,曾苛责读者的《星洲日报》中阶主管该如何非议之?假设援用马哈迪在2000年苛责“诉求工委会”的语境,能对应的词汇大概只有“奥玛乌纳”(Al-Ma’unah)了! ‖ 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