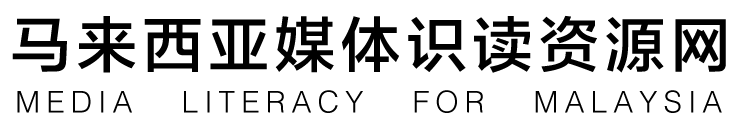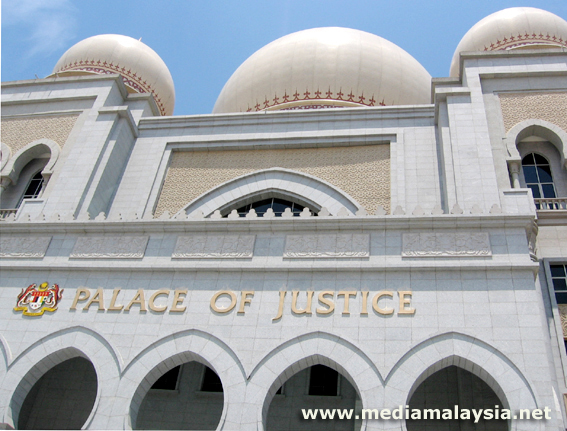
2006.12.18【光华日报·识读媒体专栏】国家是敌人,也可是工具
【庄迪澎】自由多元主义者(Liberal-Pluralist)和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似乎都认定国家机关(the State)不是什么好东西,前者视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为互相竞争和对抗的空间,国家权力扩张将大大威胁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后者则认为国家机关有剥削性。
由巫统长期垄断政权的马来西亚是个威权政体,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现实与权力运作,某个程度上都印证自由多元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机关的主张;尤其是从保障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意义上而言,国家机关制订的媒体法规长期欺压媒体,更强化了人们对国家机关的刻板印象。
不过,国家有其多重面向,它固然是压迫性的、剥削性的,但也可以是保护性的。除非你笃信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否则你很难否定国家机关的保护性职能;例如维持治安、建立公共医疗系统、立法保护历史建筑物、立法保护弱势群体等,都是国家机关责无旁贷的保护性职能。国家机关较多展现哪一种面向和职能,得看由谁驾驭国家机关、如何驾驭国家机关,以及有没有人监督驾驭者。
我国的新闻自由运动耗费许多心力在解除媒体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Sword of Damocles)――可随时吊销出版准证及无需审讯扣留的内安法令、规定每年重新申请出版准证的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强制性监禁一年的官方机密法令,以及定义范围模糊的煽动法令等等,相对忽略了争取将法律纳为己用这条路,游说、争取保障多元舆论及新闻自由的立法,善用国家机关既有的保护性职能,并削弱其压迫性。
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能兼并南洋报业控股、新海峡时报集团要兼并马来前锋报集团,以及过去四年来《东方日报》遭到四家中文报社围堵现象,正是因为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缺席所致。反垄断法阻遏反竞争(anti-competitive)行为,不只是保障同业及消费人权益,也避免由少数媒体集团主宰意见市场,这正是美国联邦政府反对大型媒体公司兼并的关键考虑,值得借鉴。
在1951年,美国俄亥俄州的《罗蓝报》(The Lorain Journal)争取经营无线电广播执照不果;不久后,联邦广播委员会发出无线电广播执照给八英里外伊利里亞县(Elyria)一家电台。为了逼使对手退出广播业,《罗蓝报》执行严厉的广告政策,凡商家在那家电台购买广告时段,《罗蓝报》将不接受他们的广告。由于《罗蓝报》渗透当地99%的家庭,当地商家别无选择,只好屈从于这种不合理作风,不在那家电台购买广告时段。
美国司法部对《罗蓝报》提出反托拉斯(Antitrust)民事诉讼,指责《罗蓝报》试图垄断商务;《罗蓝报》则辩解说,政府的行动侵犯了其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及拒绝广告的权利。最终,法院宣判《罗蓝报》非法垄断商务,并发出庭令禁止《罗蓝报》继续其反竞争商业行为。法官否决了报纸的“冒失、残酷及掠夺式的商业行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说法,也否决了《罗蓝报》有权接受或拒绝广告的说法。
《罗蓝报》一案的判决,似乎也并不出奇,因为早在1945年美联社对美国政府(Associated Press v. United States)案的法官布莱克(Hugo L. Black)曾有判词说,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新闻自由的关心解读成“一道说明政府无权保障自由的命令”,似乎很奇怪。易言之,反托拉斯(Antitrust)法律应用在媒体时,并不抵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
我国并无反垄断法,政府也不反对企业垄断,甚至还是推动企业垄断的幕后推手。要在我国游说制订反垄断法肯定知易行难,要让反垄断法成为可欲的诉求,公民社会就要扮演逆向角色,像美国司法部执行阻遏反竞争行为的职能那样,让垄断者(企业/政府)意识到,甚至一尝垄断者应付的代价,才更有可能等到反垄断法成事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