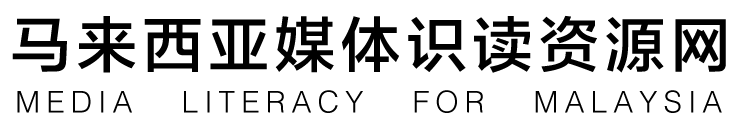2014.10.24【燧火评论】时政评论:被误解的实践
【庄迪澎】我向来认为,时政评论应是一份报纸的重要”「标记」,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业已造成新闻报导趋向同质化,未能彰显一份报纸的性格,而报章的言论版(不论版位名称为何)则能以其鲜明的犀利风格成为读者「辨认」报纸的因素。我也主张,一位优秀的记者,除了採写新闻报导之外,亦应有撰写评论的功力。
然而,曾几何时,马来西亚中文报章的言论版也已失去了应有的性格,沦为滥竽充数的园地;除了极少数比较优秀的专栏作者之外,关于生活琐事、随想、喃喃自语大行其道,甚至更糟糕的是,一篇篇「文字拼凑」——用我们熟悉的文字拼凑成一篇不知所云的「文字杂烩」——也充斥其中。原因之一,或许是对「时政评论」的界定人言人殊,准绳不一,似乎凡是刊于「言论」版位的文章,不论是读者投稿或专栏作者的作品,均被看成是「评论」,而且「评论人」的身份认定也同样宽鬆。
时评就是通俗骂人文章?
经年累月,我们于是习惯了言论版就是「大杂烩」的样子,这不是指角度和观点的多元(偏偏这是稀缺的),而是文体参杂、内容和书写功力良莠不齐。于是,很多人对「评论」的印象不外乎:抒发己见、不吐不快,甚至更肤浅的「骂人的文章」。易言之,「评论」就变成了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的想法和喜恶,乃至情绪的宣洩。随此印象而来的,恐怕就是对时政评论的不以为然了。
这是对时政评论的第一个误解,以为时政评论和评论人就是长这个样子,编辑也认为它们「应该」长出一幅「雅俗共赏、不伤脑筋」的样子。此误解之产生,有其历史脉络可循;回顾中文报业的发展,我们或可从「人才养成」青黄不接的尴尬现象窥探一二。
马来(西)亚中文报业始于19世纪,而时至20世纪初,不乏来自中国和香港的知识份子主持编务和笔政,其中既有中国旧式知识份子,也有留洋结束西式教育的知识份子,试举一二如在《叻报》服务40年的主笔叶季允、《天南新报》的创办人丘菽园,乃至较晚的《星洲日报》第一任编辑主任傅无闷(1929年至1937年在该报主持编务和笔政)等等。
然而,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中港)老兵凋零,由本土新丁接替,同时昭示了传统知识份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报业工作者。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大学教育还说不上普及,中学教育则缺乏广泛的通识学问,而课外知识的流通也因传播科技未臻发达而有限。于是,报社编採人员不论知识或语文素养,乃至理念,均已无法和前人媲美。由于缺乏研究和严谨写作的能力(除了极少数如张景云、罗正文例外),他们撰述的时评多出于对事件的常识性回应、冷嘲热讽、嬉笑怒駡,甚至只是资料整理或引述他人的论见,未能深入分析和论述。(其实报社裡不无早期新加坡南洋大学及留台的中文系和新闻系毕业生,但他们几乎都不受器重,原因何在,我期许研究报业史的同道能梳理出来。)
1980年代,报社外的作者群为数不少,而且不乏学有所成的社团活动者、文化人、社运份子和从政者,报章上的论战亦十分热烈,例如曾经为人津津乐道的1987年「知识份子升官图」论战。然而,也许是碍于对读者群识读能力的「想像」和「认定」,以及编辑的素养和视野所限,这些作者并非主力,更多的是读者投稿的泛泛之谈文章;1990年代活跃于本地中文报章言论版的政治学者何启良亦曾评述道:「大多数评论者是通人而非专才,他们可以用常识对时事作出观察、分析和选择;但是,是否有『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却是一个问号。……我们时常可以发现到许多评论文字枯燥无味,识见平凡,立论肤浅,显然是作者缺乏进修和深自砥砺所致。」(何启良,〈大马华人时事评论的重建〉,《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论述》,页141-152,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年)
到了1990年代中期,像是曾庆豹、祝家华、何国忠、何启良,以及较后的安焕然一度成为中文报章裡的学者型健笔;而后期《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分别在星期日增设《星洲广场》和《南洋论坛》专刊,刊载深度的文章,才使得言论版长出新的面貌;不过,这两个专刊毕竟只在星期日刊出,曝光率显然无法与星期一至五的言论版相比,而且历时十多年后也分别悄然停刊了(这裡牵涉报社的市场偏见和资源分配的问题)。
资讯极简钝化思辩深度
1990年代以降,虽然私立大学林立、教育普遍提高,但是学习情况日益「快熟麵化」和「死命赶」,似乎也未能培养大量的学者型评论作者。如今的情况可能更为讽刺,网络媒体从部落格到新闻网站再到脸书,这一路的沿革一再地造成知识和资讯的「极简化」——从网民爱看短文的迷思演变至只看脸书图解,甚至有能力深入申论问题的作者,也勤于在脸书写个三五句更甚于撰文议事。
对时政评论的第二个误解,是对时政评论的功能和意义的轻视。
据1970年至1984年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的资深报人朱自存所述,在马来西亚现存中文报章当中,《南洋商报》的「言论版」是在1970年10月中旬由他创设,「是以提供舆论为目的,是属于一般人发表意见的地方,容纳一切的意见(正、反各方的),但无意供个人发表『你的我的』这类个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朱自存,〈言论版度过20年〉,《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页108-109,吉隆坡:东方企业,1994年)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而言,朱自存的观点是没错,毕竟议会制当以民意为基础,而大众媒体则是传达民意的相对有效的工具,尤其是发展到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主张时,言论版作为民意交集、碰撞的公共空间,意义尤其重要。理论上报社固然会信誓旦旦地说,言论版志在「启迪民智」,让民众的声音百家争鸣,但是就现实政治而言,所谓「舆人之论」往往并非民众的自发性言论,而是经过设计、部署和筛选,以执行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化(pedagogic)任务;那些思维模煳、价值溷乱的文章,也许作者并无此主观意图,但仍然有可能成为「愚民」的工具。换言之,报社所谓的「启迪民智」,可能恰恰相反,是在「洗脑」。
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从来不是只靠着法律、警察和监狱,这些诉诸国家暴力的手段主要是在遭逢重大权威危机的非常时期派上用场。然而,各种保守、能帮助统治者的地位长治久安的言论,不管在太平时期或是权威危机时都在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即便是最忠诚的在野党人,不论是在马哈迪、阿都拉或纳吉统治的时空裡,批评政府时也不自觉地随着官方论述起舞,言必「某某做法,马来西亚将无法实现2020年宏愿」、「某某狭隘的思维,不符合阿都拉的文明伊斯兰(Islam Hadhari)理念」、「某某偏差,不符合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1Malaysia)理念」云云;虽然力竭声嘶反对《煽动法令》,却也乐此不疲地举报政治对手煽动。这些按照国阵的语言框架和行为模式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恰恰印证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以积极同意(active consent)为基础的文化霸权(Hegemony),以及阿图舍(Louis Althusser)类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正在发挥「维稳」作用。
时评体现政治参与实践
据此意义申论,时政评论就不仅止于表达个人的喜恶感受或传达舆人之论而已。言论版是一个政治场域,时政评论亦是有所图的政治参与和实践。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它应有意识地以破解保守成见和官方意识形态为己任,同时提出进步的主张和理念。虽然「启迪民智」之说多少带有精英的味道,但鉴于马来西亚社会整体人文知识素养未臻理想,时政评论的实践者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应以此为己任,促进文明的提升,始能期许营造一个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动员(而不仅是政权更替)的社会。
在这反面,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我们做得并不够。反观,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文字兵团却充斥着言论空间,甚至再烂的作者也可以同时在三、四家报纸写专栏。我们做得不够,其中一个原因是出自对时政评论的另一种误解或偏见:写作只是纸上谈兵,实际参与社会运动才是王道。这种误解或偏见,恰恰是因为人们没能意识到时政评论应有前述的更重大任务。
公民运动,尤其是在非常时期走上街头,当然重要,但是与之并行的知识的生产,也是同样重要的「行动」;以净选盟(BERSIH)为例,从2007年至今,除了经历了三场大规模示威,后续的选制改革的主张、设计、讨论,以及经由公共空间广泛宣导,甚至挑战官方的选制不改革说法,难道不是相辅相成?时政评论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它提出主张并不意味着就是空谈,而是对政治和政策变革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和想像,这个社会才能说上多元。 ‖ 原文出处 ‖